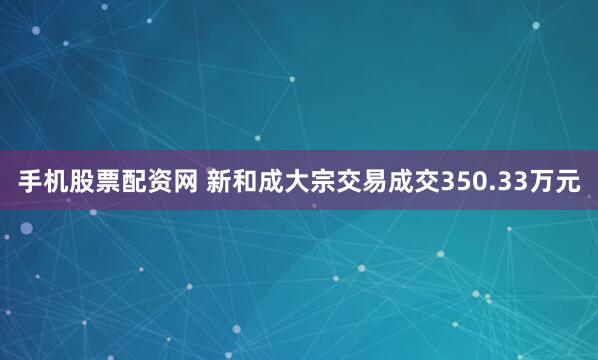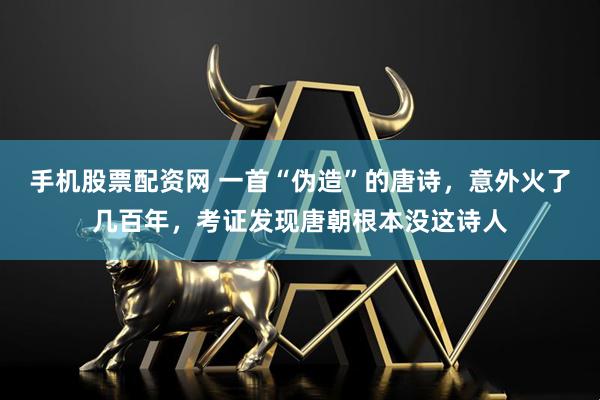
康熙四十五年(1706)手机股票配资网,曹寅主持编纂的《全唐诗》正式问世。
这部耗时一年半、收录近五万首诗作的典籍,一度成为古典诗歌的权威标杆。
但很少有人知道,书中一位与李白、杜甫并列的“盛唐才子”牟融,带着六十九首“唐音”火了数百年,最终却被考证出唐朝压根没这号人。
初次得知这个消息时,我着实吃了一惊。
毕竟牟融的诗作,不少人在课本里都接触过。
他的《客中作》“千里云山恋旧游,寒窗凉雨夜悠悠”,读起来格调高古,辞藻俊朗,怎么看都像是盛唐山水诗的典型。
展开剩余85%可就是这样一位“名家”,在唐代的典籍、碑志、笔记里,连一点踪迹都找不到。
《全唐诗》里的“穿越诗人”《全唐诗》的编纂过程其实挺仓促的。
当时十名翰林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了九百卷的内容,收录标准也相对宽松,只要诗风贴近唐代、题赠的人物有迹可循,基本就能“放行”。
牟融的诗作恰好符合这些条件,于是便堂而皇之地跻身其中,连小传都写得有模有样,标注为“贞元、元和间人”。
本来想,既然能被《全唐诗》收录,履历应该没啥问题。
但后来发现,牟融的诗作里,漏洞简直藏都藏不住。
他的“朋友圈”时间线乱得一塌糊涂,既给开元、天宝年间的书法家徐浩写过送别诗,又为宝历年间才中进士的朱庆馀赋诗饯行,中间足足隔了上百年。
这搁现在,妥妥的“穿越剧剧本”啊。
他诗中提到的画家范启东,在唐史上查无此人,反倒和明代永乐年间的画家范暹同名同字。
这样明显的“穿越”痕迹,放在以严谨著称的清代翰林眼里,本该一眼识破。
可当时编纂者只盯着“诗似唐”这一点,竟让这位“明人”稳稳坐上了唐诗的“贵宾席”。
其实古代典籍编纂,类似的疏漏并不少见。
毕竟在手抄、雕版的时代,文献传播全靠人工抄写、整理,缺乏系统的复核机制。
加上时间紧、人力有限,很多典籍都难免出现误收、漏收的情况,这也为伪作混入正统典籍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伪作如何混进经典顺着这些漏洞往下查,牟融诗作的真实来源逐渐浮出水面。
这些被当作“唐诗”的作品,压根不是唐代产物,而是明代中叶的“仿古之作”。
早前明代中叶,前后七子高举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的大旗,全社会都掀起了模仿唐诗的热潮。
当时的文人都以能写出“唐音”为荣,诗作在遣词、句式上都刻意贴近唐代风格。
这种全民仿古的风气,确实为伪作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文化土壤。
有需求就有市场,书商们嗅到了商机。
他们把明代文人的仿古之作,伪题为“唐牟融”,通过明抄本的形式流传。
这些诗作本身艺术水准不低,再加上“唐诗”的标签,很快就受到了藏书家的青睐。
明末藏书家季振宜把这些诗收入了自己私辑的《唐诗》中,而这部书后来又成了《全唐诗》的底本,牟融的诗作也就这样完成了“正典化”的过程。
搞不清的是,这种造假链条在当时竟如此顺畅。
明人仿古写诗,书商伪题作者,藏书家收录,再到清代翰林编纂时盲从,一步步让伪作变成了“经典”。
更让人意外的是,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。
元末明初人唐温如的《题龙阳县青草湖》,因“醉后不知天在水,满船清梦压星河”的绝美意境,长期被当作晚唐佳作,直到后来才被考证出真实年代。
并非明智之举的是,当时的书商为了牟利,伪造古籍的现象十分普遍。
除了诗歌,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,都曾出现过伪托前代名人的作品。
这些伪作之所以能流传,一方面是因为模仿得足够逼真,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人们对前代经典的盲目崇拜。
要说这些伪作能火几百年,绝非偶然。
首先,它们的艺术水准确实在线。
牟融的诗语言洗练、意象清空,就算放在真正的唐诗选中,也毫不逊色。
其次,唐诗的“品牌效应”太过强大,后世对盛唐诗歌的集体崇拜,让人们天然愿意把佳作归入唐代。
更何况,唐末五代的战乱导致大量文献散佚,也为伪作“补位”创造了空间。
如今,牟融的名字已经被《全唐诗》新版附录移出,多数高校教材也加了“明人伪托”的注释。
但在一些短视频平台、通俗读本里,“唐代冷门诗人牟融”的标签依然存在,不少人还在为他的“唐诗”点赞转发。
个人觉得,辨伪并非要否定这些作品的价值。
毕竟诗是假的,情感却是真的;时代是错的,美却是对的。
我们真正该做的,是建立“知人论世”的阅读习惯,读诗前多查查史籍,看看诗人是否“有迹可循”。
同时也要明白,经典的魅力不在于“招牌”,而在于文字本身穿越时空的力量。
当我们再次读到“浮亭花竹频劳梦”这样的句子时,不妨在心底轻轻更正:这是一位不知名的明人,隔着三百年的月光,向盛唐递出的手掌。
让“牟融”回到明代,让唐诗继续做唐诗手机股票配资网,这或许就是考据与审美最好的和解方式。
发布于:山西省亿通速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